热点新闻
民间融资的罪与罚――记光华法学院第五期刑法前沿论坛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 发布日期:2012-02-20 点击次数:2897
民间融资的罪与罚——记光华法学院第五期刑法前沿论坛
2012年2月15日,在吴英案二审判决结果引发全国舆论汹汹的背景下,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主办的第5期刑法前沿论坛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拉开帷幕。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楼伯坤、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艳霞、浙江警察学院教授张俊霞、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沈琪、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讲师张伟,以及我院刑法点副教授高艳东、诉讼法点教授胡铭、民商法讲师陆青以及学院广大同学参与了本次论坛。本期论坛以“民间融资的罪与罚:以吴英案为例”为题,主要围绕吴英案和民间融资发展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院高艳东副教授主持了本次论坛。

讨论伊始,楼伯坤教授率先亮剑。他认为,吴英案不是单纯的个案。我们应该将视野放宽到对整个集资类案件中讨论。对此,楼教授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
第一,诈骗罪的种类划分及相互关系。楼教授认为集资诈骗罪从形式上看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但诈骗罪是自然犯,而集资诈骗罪已不再是一种自然犯,而是兼有自然犯和行政法双重属性的混合形式。诈骗罪的行为特征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因此当单纯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不能成为某种特定诈骗罪的罪状时,该类犯罪就不是诈骗罪了。他建议立法应取消所有的特定诈骗罪,只设一个普通诈骗罪即可,以行为来决定犯罪性质。
第二,非法集资罪的罪刑结构分析。楼教授认为如果特定诈骗罪的设立是为了满足犯罪客观特征的特殊性,那么,它应当遵循普通诈骗罪的罪刑均衡要求。从普通诈骗罪中产生出来的罪,其配刑反而高于诈骗罪,这是不科学的,应该将集资诈骗罪的配刑范围限缩在普通诈骗罪的范围之内。
第三,就吴英案本身而言,因没有看过具体材料,不能得出具体的结论。但从媒体披露的判决文书来看,楼教授认为吴英主观上非法占有的故意不明显。即使某一笔或某几笔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也只能认定主观占有故意明显的那部分为集资诈骗。此类案件认定非法占有的故意,关键要看出现欠款时的实体资产总量及两者比例。同时,对于挥霍行为,也要看其挥霍资金与所吸收资金的比例。从现有情况看,吴英案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更为恰当。
继楼教授的发言之后,杨艳霞副教授开门见山地抛出了自己与楼教授截然相反的观点。鉴于没有看到全部的案卷,所以杨老师就浙江省高院的判决书来谈一些看法。杨老师认为如果判决书列举的都是事实,那么这个判决并不是像网络上所传言的那么槽糕。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的区别主要有三点:第一,在借款手段上,是否如实告知借款人本企业的情况,是否存在欺诈;第二,在借款用途上,是将借款用于企业经营,还是用于其他借款的还本付息;第三,在资金来源上,是向特定的关系人借贷还是向不特定的对象借贷。从这三点出发,杨老师认为,吴英的很多集资款在主观上存在欺诈。她在集资时使用了欺骗手段,又将集到的资金用于偿还前面的利息。集资诈骗的重要特征就是用后面集资的本金偿还前面集资的利息。吴英借款的资金来源也是不特定公民。因此,吴英的行为应当成立集资诈骗罪,省高院对本案的定性并无不当。
在量刑发面,杨老师也认为虽然《刑法修正案(八)》依旧保留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在现有法律内判处吴英死刑也符合法律规定,但仍然反对对吴英处以死刑,因为对经济犯罪判处死刑表现出对生命的不尊重。
最后,杨老师就吴英案提出了几点思考:第一,吴英未携款潜逃并不能证明吴英就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考虑非法占有的表现形式。第二,集资诈骗的对象是有钱人同样对社会具有危害性。第三,对吴英判处死刑并不能阻止“吴英式悲剧”的重演。引用一句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吴锦良教授的话——实业至上。只有整个社会克服一夜暴富的心理,坚持实业经济至上才是解毒良药。
面对前两位教授观点的针锋相对,张俊霞教授以其一贯的幽默语言阐述了其对吴英案的看法。她指出,吴英案是件可喜、可悲、可叹的法治事件。喜在吴英案必将成为推动我国法治进步的又一重要事件;悲在身处21世纪中国的吴英还要用其生命为债务买单;叹在社会各界对吴英案的关注,足见我国公民对生命权前所未有的尊重。她进一步指出,从实然角度出发,吴英案的判决是法官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司法的结果,无可厚非。而从应然角度出发,经济领域内犯罪存在死刑是不合理的,吴英不应用生命为其债务买单。
紧接着,来自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的张伟博士,从刑法之中、刑法之上和刑法之外三方面对吴英案进行了分析。
首先,从刑法之中。张博士站在刑法解释学的角度,认为吴英案有四个焦点值得关注:第一,集资对象的公众性;第二,吴英吸收公众资金具有“非法性”;第三,难以明确吴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四,社会上的一夜暴富心理是由于我国金融政策不稳定的客观环境造成的。
其次,从刑法之上。张博士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吴英是否罪大恶极,必须处死;第二,以刑罚手段来对付民间集资问题是否必要。
最后,从刑法之外。张博士认为第一,泡沫经济是滋生投资心理的天然场所,吴英案绝非个案。第二,权威的司法判决与民众态度截然对立,司法公正必须减少政治因素的渗入。
沈琪副教授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并结合其律师工作中所接触的类似案件,提出我国民间融资法律地位不明、融资方式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是吴英案判决引发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进而指出,吴英案的很多地方存在牵强之处,例如判定吴英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沈老师还指出,企业在欠债的情况下集资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以后款来偿还欠款的行为是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不应认为是未用于企业经营。
胡铭教授认为吴英案从实体的角度来看,争议很大,如对什么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社会不特定对象”等,而我们从程序的角度,也许可以另谋蹊径。具体而言,首先,从民众参与司法的角度,如何弥合普通民众与司法机关的鸿沟,使得司法裁判反映所谓的一般社会正义观,需要通过程序解决,如陪审团为解决类似吴英案这样的棘手案件,有很大的优势;其次,我国学者虽然一直在强调“无罪推定”,但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践行,而“疑罪从轻”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如美国就类似制度。吴英案在证据并非十分充分的情形下,对其判处死缓或其它更轻的刑罚,应该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一种结果;最后,死刑复核制度在我国被长期以行政化模式运行,书面审理难以对案件做准确判定,死刑复核的诉讼化是改革的必然趋势。可以考虑将死刑复核庭改造成巡回法院,对重大刑事案件做最终判决。
陆青博士结合个人从民法角度学习民间借贷问题的认识,指出当下人们在看待民间融资司法规范上更多关注刑法上的罪与罚问题,建议理论界同样应该关注民法在调整民间借贷问题上的积极作用,并认为解决民间融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包括刑法和民法),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流向实业领域而非投机领域。

高艳东副教授在认真聆听了以上专家的发言之后,提出了自己对吴英案和民间融资的几点看法:
第一,浙江民间借贷市场急需“打黑治腐”。从历史经验看,高利贷背后往往伴随着黑社会和公权力两种因素。而黑社会多以公权力为保护伞,所以如何防止公权力渗入民间融资领域才是法律人关注的重点。浙江高利贷有其特殊性,民营企业被黑社会和公权力“绑架、挟持”虽然是偶发现象,但对健康市场经济危害很大,甚至可能发展成黑色经济体或地下权力系。
第二,对于诈骗应当进行缩限性解释。传统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冒险经营行为都可以按照犯罪处理,这给司法机关的选择性执法提供了条件。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多数经济犯罪的处理结果,我们会发现,并非资本具有原罪,而是法律充满原罪。刑法学者的任务是将一些可以作为民事欺诈的行为从诈骗罪中剥离出去。身份真实、公开的诈骗是发生在平等主体间的争端,受害人与欺诈者能够通过私法途径解决,应先按照民事诉讼处理,本着“先民后刑”的原则。对于经济风险,刑法应该有选择性地介入。
随后,论坛进入自由发言阶段,同学们围绕诸如“集资诈骗的形成过程如何界定”等问题与专家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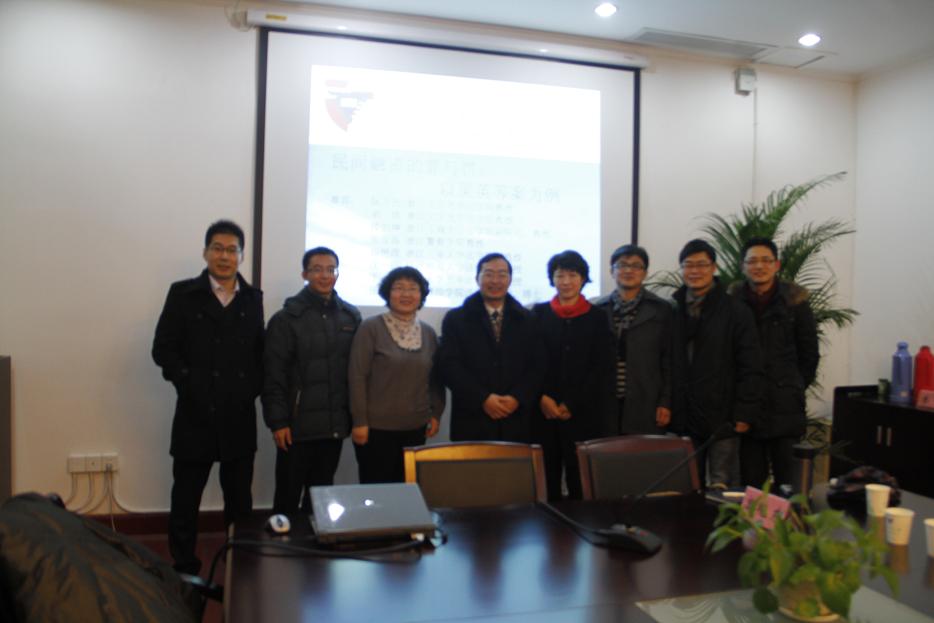
吴英案的二审判决已交由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等待她的将是囹圄铁窗抑或生命终结我们不得而知,而吴英案对中国法治建设和民间融资的影响却是可以想象的。关于吴英案的论坛已经结束,但对吴英案的讨论将不会结束。
文/陈旭 图/朱佳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