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新闻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正在形成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 发布日期:2013-02-25 点击次数:1006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正在形成
钱弘道
(本文是钱弘道在2012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的演讲,后在2013年2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法学网、光明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等转载。)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对法治有强大的需求。政府官员、学者以及社会其他各阶层走到一起,共同推动中国法治发展;其中,学者的作为引人注目,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以浙江为例,这些年,一大批学者齐聚浙江,为“法治浙江”、“法治中国”出谋划策。在众多学者的参与下,浙江出现了一系列法治创新实践。法治指数、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就是在一批学者与政府官员、社会各阶层全面互动下完成的。
一、法治指数是“法治浙江”的一个大胆制度创新实践
2006年2月8日,春节刚过,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赴杭州市余杭区调研,主题是“法治浙江”。之后,余杭率先在浙江提出“法治余杭”规划。浙江在全国较早提出建设“法治浙江”的战略决策。从2006年年初开始,北京、上海、浙江、香港等地的一批专家学者纷纷将注意力投向杭州余杭。
余杭启动了“法治系统工程”,这项工程以法治指数为引线和枢纽。此后,余杭在全国推出第一个全方位的法治评估体系,出台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余杭法治指数研究是全新的、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研究。六年多来,这项创新研究及其实验成果被众多新闻媒体报道,引起了社会上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热烈程度和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程度超出了预想。围绕“法治指数”的实践和讨论被媒体称为“法治指数现象”,余杭被称为“全国法治试验田”。余杭法治指数被评为“浙江省改革开放30年百件典型事例”。
法治评估能有效培育公民的法治观念和精神,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促进社会的民主和法治转型。实践表明,通过以法治指数为引擎实施“法治系统工程”,余杭区的公民法治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法治余杭建设的责任感不断增强,公共权力得到更有效的限制,从而为中国其他地区的法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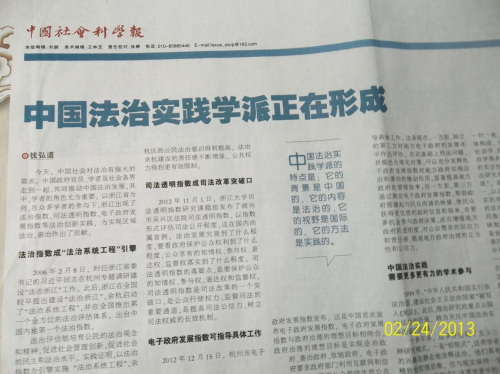
二、司法透明指数是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的长效机制
2011年8月2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深入推进阳光司法专家意见征询会”。有学者在会上提出了测定司法透明指数的建议。浙江省高院齐奇院长在会上当即回应,充分肯定了测定司法透明指数在“阳光司法工程”中的长远意义。之后,司法透明指数成为2012年浙江省高院的重点调研课题。浙江大学受浙江省高院委托,开展司法透明指数研究,并选取浙江湖州市吴兴法院为实验点。2012年11月1日,在“司法透明指数论证会”上,课题组发布了吴兴区法院司法透明指数。以指数形式评估法院的司法公开程度,这在国内尚属首例,也是中国学术团队首次向世界公布中国的司法透明程度。
法治发展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要看政府保护公众权利到了什么程度,公众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到了什么程度。司法透明指数的根本落脚点是要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司法透明指数是司法改革的一个突破口,是公众行使权力、监督司法的理性通道,是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的长效机制。
司法透明指数实验契合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更加注重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的精神。司法透明指数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它是中国共产党转变执政理念、中国司法改革推进的结果,也是世界范围内社会指标方法广泛应用的结果。
为什么司法透明指数会产生在浙江?第一,浙江作为中国先发地区,法治走在全国前面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先发地区,法治可以先行。第二,浙江省高院推出“阳光司法工程”,并且做得有声有色,在司法公开方面做出了表率。第三,余杭法治指数客观上推动了司法透明指数在浙江的产生。法治指数事件推动了一个区域和全国法治的进程。司法透明指数实际上是法治指数的拓展性研究。第四,司法透明指数的产生与领导的决策是分不开的。学者的智慧必须与领导者的远见卓识结合,才能变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中国社会特别需要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
三、电子政府发展指数推动法治政府、善治政府、效能政府的实现
电子政府发展指数,也可以叫做政府透明指数。在杭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浙江大学、国际善治、中国法治研究院合作完成了中国电子政府发展指数课题第一个阶段的研究。2012年12月15日,杭州市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在“中国法治国际会议”上发布,这是中国首次发布电子政府发展指数。
电子政府发展指数与政府治理的理想目标相吻合。政府治理的理想目标是实现法治政府、善治政府、效能政府。电子政府要求政府部门利用因特网和信息技术,面向公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充分体现政府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透明化和高效化,充分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效由人民检验”的指导思想。所以,电子政府发展指数所反映的一系列理念是“民主民生”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法治和善治的必然要求。
电子政府发展指数的测定是一种管理创新。指数测定工作不是为评估而评估,不是现状的传声筒,而是要在实践层面上指导具体工作。这表现在:一方面,独立的第三方对地方电子政府的发展水平做出评估,在此基础上找出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对策,能充分发挥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对地方政府实现法治和善治的重要推动作用,能显著提高地方政府的管理效率;另一方面,第三方通过测定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帮助政府搭建起与民众之间互动与沟通的桥梁,使民众获得更优质的政府信息与服务,有更多机会参与政府决策,能增强地方政府的透明度、对公众需求的回应力以及责任感,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的正当性和公信力。
通过项目研究和实施,杭州地区积累丰富的经验,这有助于充分发挥先行地区的引领与辐射作用,促进电子政府在全国范围的发展。可以预测,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将发挥示范效应,促进我国实现治理现代化,加快与国际接轨的速度,提升国际形象和影响力。
四、中国法治实践需要更多更有力的学术参与
在浙江相继诞生了中国首个法治指数、首个司法透明指数、首个电子政府发展指数,一系列创新实验符合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法治浙江”要“深入人心、惠及群众,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的要求,是“法治浙江”的理论深化和实践创新的见证,是中国法治模式的重要探索,在全国起到了良好的引领作用。2012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法治建设的浙江探索(见证)》。文章说,浙江在全国率先尝试发布一个县域范围内的“法治指数”,率先创新设立“司法透明指数”,率先实现在全省所有行政村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等等,一系列耀眼数据和创新举措,勾勒出“法治浙江”建设六年多来的稳健步伐。
中国的法治进程以1999年划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写入《宪法》。于是,理论研究的重点从探讨法治的价值转为关注法治实践面临的种种问题。中国法治研究开始发生重大转型,学者们开始试图寻找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
这十多年来,法学界实际上出现了至少三种研究模式。一是“经院式”,这类学者的兴趣是静态地诠释法治,他们或许具有精致的哲理思维,但书卷气比较浓厚,与现实隔着距离。二是“批判式”,这类学者中的一些人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他们有时也被称为“自由派”。《环球时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名为《自由派应为社会团结有所建树》。文章说:“中国社会形成今天的多元局面,自由派是有贡献的。”但也提到一些学者的看法:“理论研究几乎没有进展,更热衷‘政治博弈’。其对西方理论过于臣服。”第三种是“实践式”,他们积极参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与政府、社会各阶层联手共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我们可以用一个新名词来概括第三类研究模式,即“法治实践学派”。中国正在形成这个学派。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它由一个包容力极强群体构成。他们致力于制度创新,组合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多种学科的力量,追求法治研究的实证性和实践性。从事中国法治研究的一个颇具规模的知识群体,之所以被称为“学派”,当然应当具备学派应有的特点:第一,以法治为研究对象而形成求真务实的学术传统;第二,研究紧扣中国的法治实践,并与政府、社会各阶层共同推进中国法治发展;第三,不是津津乐道于一味的批判,而是更多地强调建设,特别是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第四,具有国际视野,参考古今,博稽中外,融会贯通,不存偏见,吸收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法治研究成果;第五,在民众参与还不那么充分的转型期,这一派学者对中国法治的发展将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概而言之,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特点是:它的背景是中国的;它的内容是法治的,它的视野是国际的,它的方法是实践的。即使今天这些特点还不那么明显,但将来一定会彰显出来。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我们的目标是“法治中国”。法治中国的道路没有现成的答案。这就需要有更多的法学家走进实践,探寻中国的法治道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符合当今中国的法学研究趋势,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学者和政府、社会各阶层合作,并形成合力,能够实质性地推动中国法治,这是中国法治发展需要的主要推动力;并且,此类研究也最符合中国转型期的实践需要。这就是“协同创新”。在这样一个发生巨变的中国社会,中国法学界应该出现学派。转型期的中国,特殊的国情已经成就并将继续成就法治实践学派的特殊作为。今天的法学家们应该做出一些承先启后的事情,这是时代赋予学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